Letter 10:一个写自己的人,和一只猫

四月,我的潮汕书写作差不多来到一半,每天都要关在郊区的房间里,试图获得一些文字上的突破。
没想到,和我关在一起到,是家庭的新成员,一只紫金渐层英短小猫。
猫伏在那里,又一次试图靠近我。它的尾巴刮过我的脚踝时,像一把刷子。我是这个家里和它共处时间最多的人,因我是"坐家",在家里写作。
是小创和果然把它从商场的宠物店带回家的。小创回忆了一下自己是在哪一刻下定决心要收养这只小猫的?大概是和店员道别,已经为她们而加班了半小时的店员也有点懊恼,而再回看那只小猫,它的猫生改变或者不改变,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。它已经七个月,再卖不掉,可能会被拿去配种,甚至处理掉。
于是,我三四月间在家的生活没有宁日,它不断制造出各种响动。清明节假期,母女旅行去了外地。我成了全天候照顾小猫的主人。我没起床时,它会在房门口叫我,大概是肚子饿了。而当我给它喂猫粮和换水之后,它对我的感情又多了一分。它正在建立一种期待。而我还在抗拒这种期待。

对一切都好奇的小猫
到现在,我还是没有抱过它一次。我对这团毛毛的东西躺在我的臂弯里没有向往,我甚至拒绝建立和它进一步的亲昵。我只偶尔摸过它的毛发,它就立即表示出很享受的样子。在我写作的时候,它会来到我的脚下,躺下,露出它细软的肚子,期待我和它互动。
现在,它越发喜欢跳上我的书桌,闻闻我的咖啡杯,嗅嗅我的书。它在书桌上来回踱步,让自己彻底占据我的视野。我的写作本身就艰难,气不打一处来。一只猫被困在房子里,就像我被困在文字的漩涡中。谁更自由呢?

猫观察着窗外的鸟
每天早上,我从睡梦蒸馏出来的清醒心境中,开始动笔。写的时候,我可以望见窗外,院子连着的一片小池塘,偶尔有白鹭在池边歇脚。一只黑毛杂黄毛,和一种黄毛而瘦小的流浪猫,会把我们的院子当作它们的自由土地穿梭而过,在积水的空花盆喝上几口。
时间在这片池塘上凝滞,一切没有变化,除了迎面吹来的风不再寒冷,鸭子们还是在戏水,温度对它们也没有影响。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做,一天很容易失去。而外部世界正一天天地纠缠。但我的笔下仍然只写着过去,我似乎对写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兴趣不大。过去的一切,因为时间拉开的空洞给了我重新排列、讲述的自由。
一个不断重复的动作是,我试图删掉书稿里大多数概括的句子。它们挤在段落中,像冬天地铁车厢里臃肿而颜色单调的羽绒服,只有脱掉它们,才能露出内里鲜艳的毛衣。我试图让每一个句子,回到它们所描述的生命现场,就像发生在今天一样。这是书写过去最合理的方式。
在46岁生日到来之前,我已经成为一个"写自己"的人,虽然写好自己并不容易。但,这确实是一件很小的事,比起这个世界每天在发生的,丑闻、讨薪、贸易战、吃瓜、融资、AI……它太不大众了。
我在写潮汕,一个叫做家乡的地方,一个有海岸线的地方而我童年却很少见到海的记忆,一些跨海而来的外国传教士,一些父辈渡海去当知青,他们后来被迫下海,而今天人们热衷出海,年轻人开始跳海。我不知道这些对读者有什么意义,但是相信他们会在某一段叙述中,看到曾经的自己。
小创送我一个在景德镇做的杯子做生日礼物。这个杯子做得很特别,不是传统的圆形,而是有双手可以捧住的弧度,杯口一圈红色不整齐,但能看到涂画的笔触。它是任何市集买不到的杯子,在杯身可以看见当时的模样,被烈火烤过之后长时间停留的现场,这不就是无形记忆的有形化么?写作也是这样。记忆停在那刻,凝望着此刻的我。

46岁这年,父亲开始下岗,他和克林顿是同龄人,后者在46岁这年当上美国总统。今天,我46岁,我意外地被拥有了一只猫。
最近,三明治尝试了一些新的写作项目,也很不容易。不过也有很喜欢的新尝试,像我的朋友Melissa Wan在三明治开的Writing Sex & Intimacy工作坊,就很成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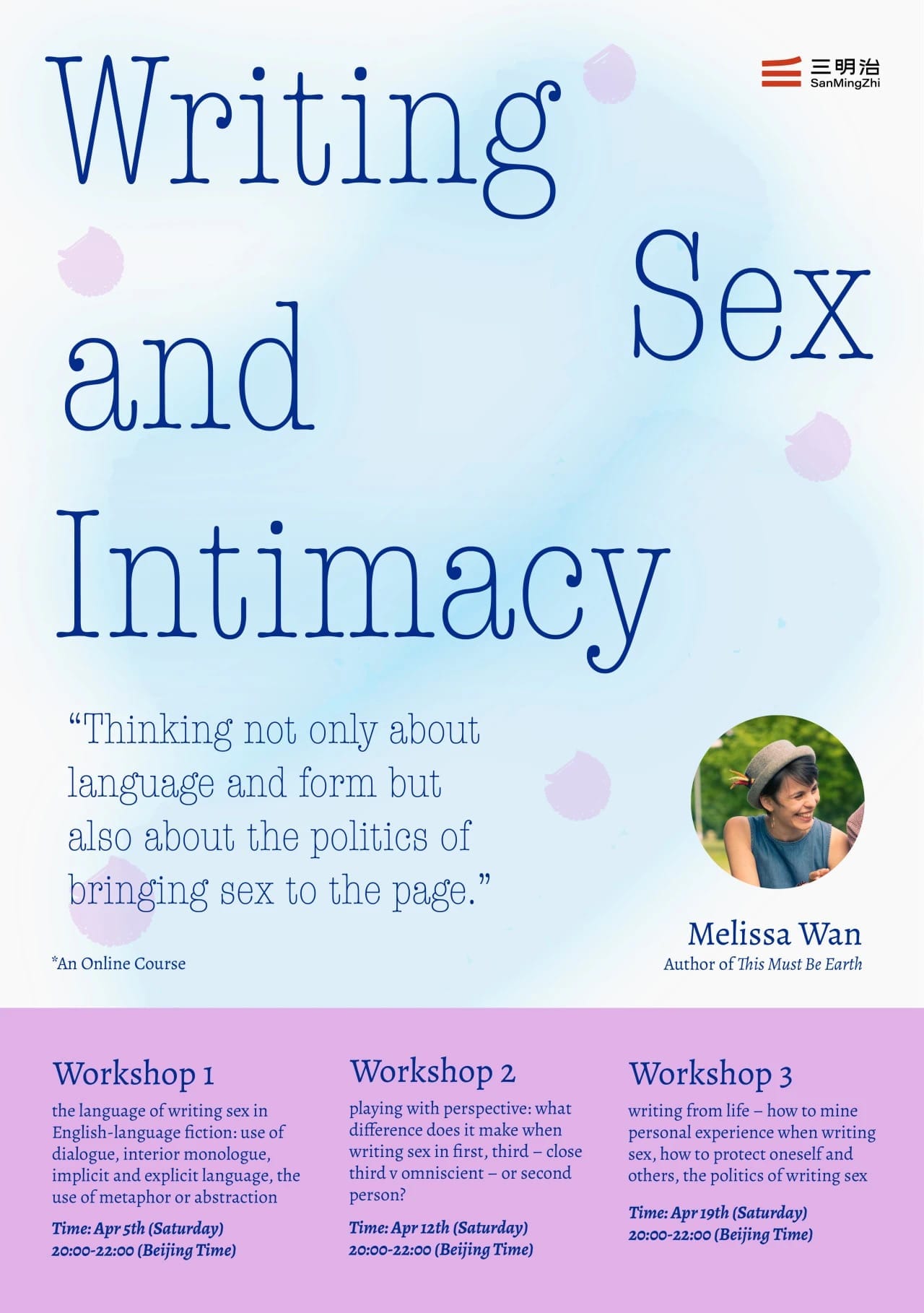
不过似乎还有勇气写非虚构的朋友在变少,尤其是第一人称非虚构。我在想,我是不是要在短故事的基础上,开出自己的第一人称非虚构工作坊呢?结合我在UEA所学到的内容,为今天中文世界的非虚构定义做一点探索。
“在场”非虚构奖学金的第五季,我也会继续担任初审评委,报名将在5月1日截止。欢迎朋友们要抓紧时间。期待能碰到多样的非虚构写作题材!去年我初审中选出的作者糜绪洋,最终成为第四季的一等奖得主。
我和作家三三一起研发的“虚构短故事”项目,5月1日即将开始第二期,也欢迎朋友们能来尝试在14天内写出一部短篇小说!(点击海报可了解详情)

我还开发了12-16岁青少年的英文创意写作项目,和我UEA的同学Julia Hollingsworth一起指导来自6个国家的8个孩子,在12周里写作两部作品。这个项目,我们在暑期和秋季都会继续做下去。(点击海报可了解详情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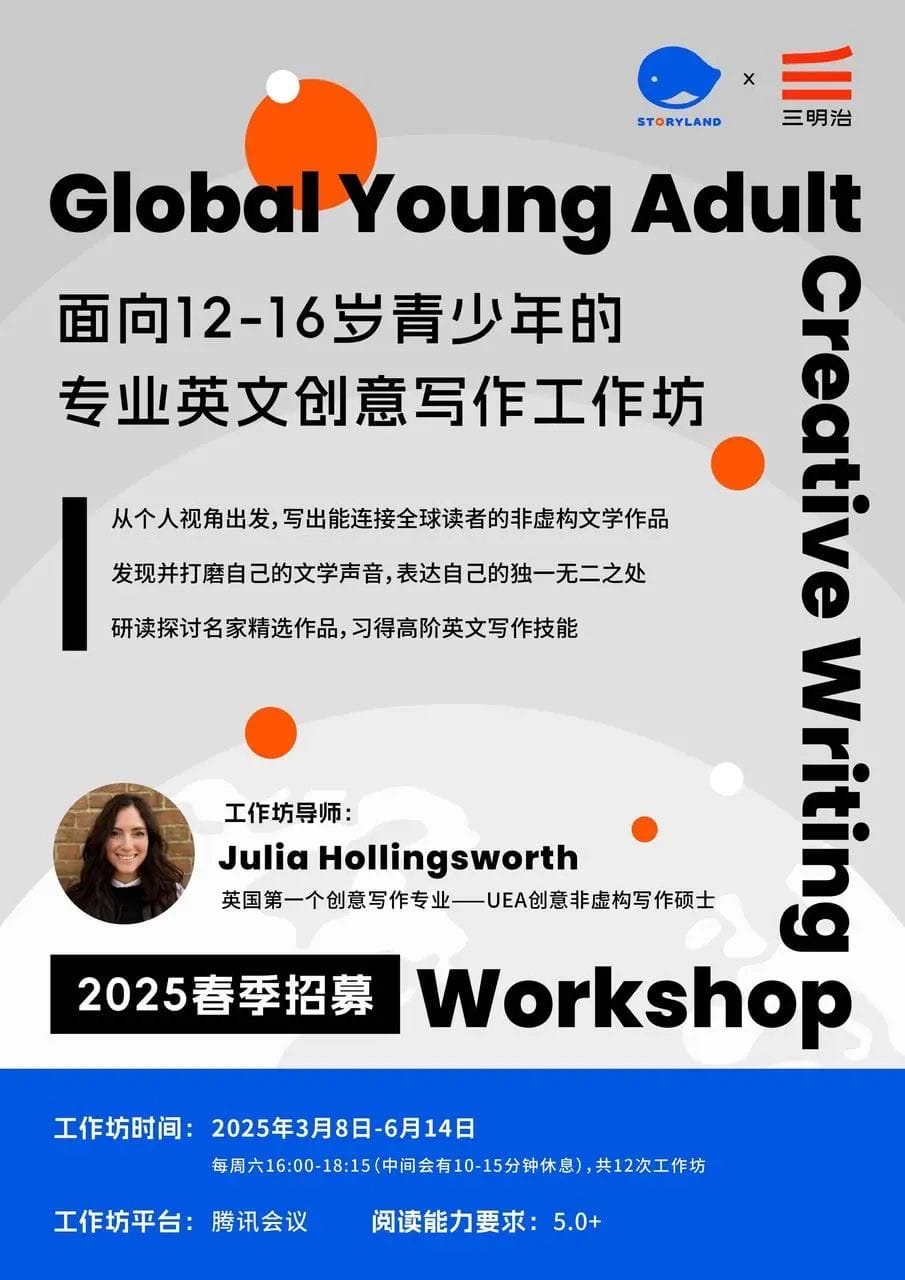
这个Newsletter, 我会努力保持更新!接下来会恢复我的阅读推荐栏目!回国之后,能够参加现场的英文写作活动就变少了。不过,我和同学们创办的Bluebell Magazine已经完成了审稿工作,多国作者的作品入选了,会争取尽快出版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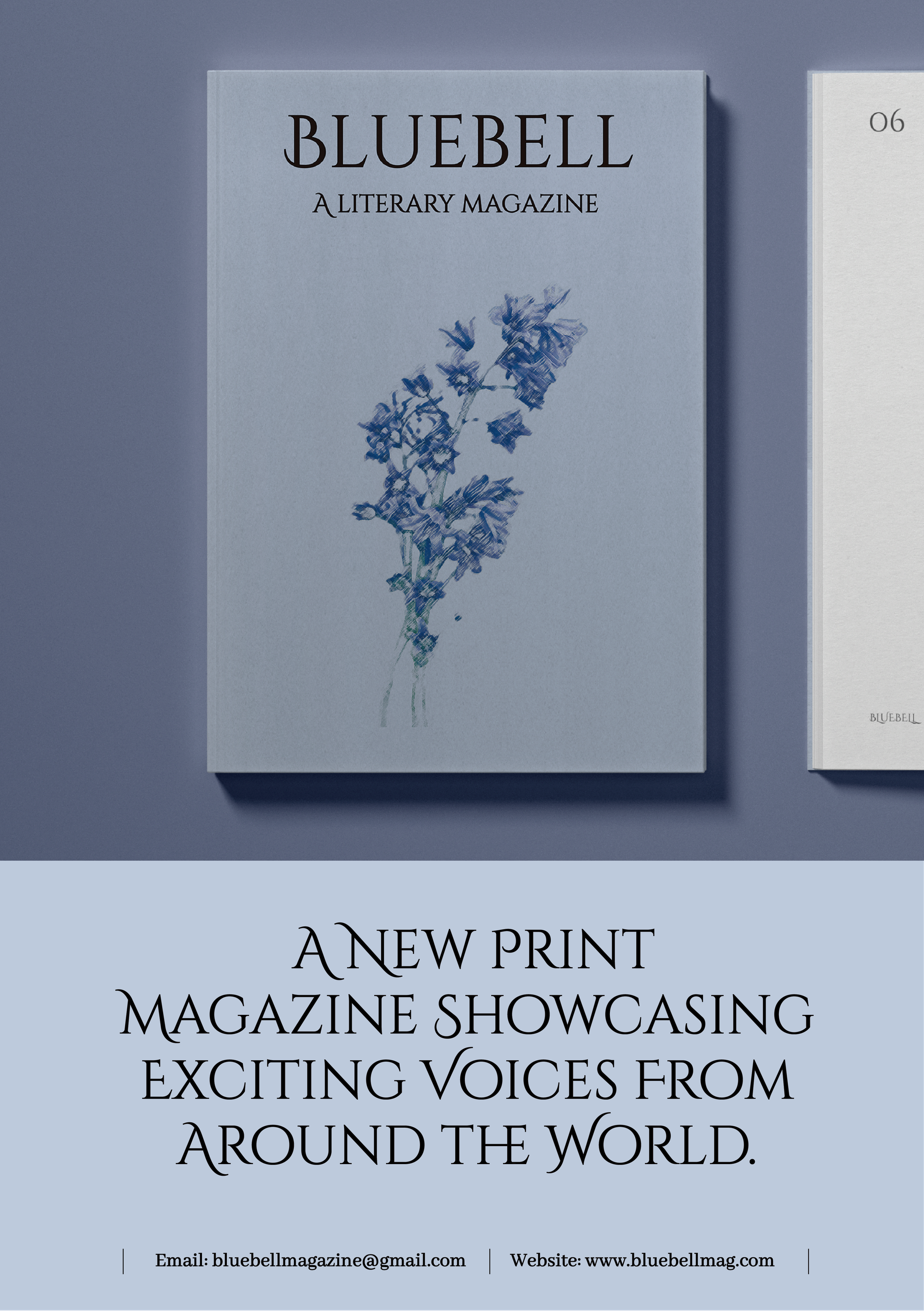
Bluebell Magazine
Forthcoming July 2025